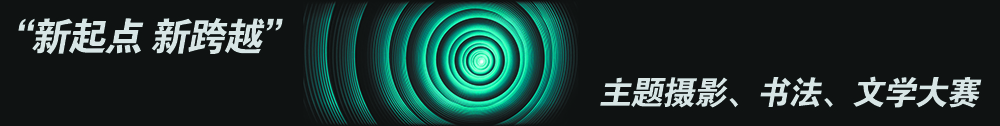屋外的细雨淅淅沥沥,在微风中缠绵飘落,屋檐下雨珠滴落如悬挂的珠帘,落地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。远处是绿油油的田野,庄稼在雨中静默如画;更远处连绵的山峦,在如纱的雨幕中若隐若现,绰约如美丽仙子。30年前的我,正忘情于这雨中世界。
“老大,你爸来信说,让我们全家都搬到宜昌去,彼此有个照应,你们在那边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。我想过去,你看呢?”母亲的话语将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。
“可我们这儿的房子咋办?这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砌起来的啊。”我说道。
“这里的房子交给你大伯照看吧,我们在那边会有新的房子。这事就这么定了,等你们姐弟仨放寒假了就走吧。”母亲很干脆地把这件有可能改变我们命运的大事决定了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就这样,母亲的一个决定,让我们全家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10年的美丽村庄。在1985年的寒冬腊月的一天,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我们来到了经常听母亲提起的那座熟悉却又陌生的城市——宜昌。而今,30年弹指而过,那栋承载过我酸甜苦辣日子的简陋平房终究停留在了记忆深处……
船上的日子
初来宜昌的我们满是新奇。一下车便看到一年多不曾见面的父亲正朝我们走来,我们姐弟三人飞也似的朝父亲扑去。
“爸爸,我们的新房子在哪里啊?”我迫不及待摇着父亲的手问到。
“噢,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呢,你们先住爸爸工作的轮船吧。”
“你在什么单位?为什么会在船上工作啊?”
“我在葛洲坝工程局啊。我们的船主要是挖砂,把砂挖出来再去建大坝。”父亲似乎是很骄傲地说到。
“葛洲坝,我知道的,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过,书上说葛洲坝是万里长江第一坝,是毛主席让建的啊。”我得意的向父亲“卖弄”着。
“是啊,葛洲坝就是我们单位修建的啊。爸爸也参与修建了呢。”父亲言语中满满的都是自豪。
父亲的船停舶在庙嘴,他将年幼的弟弟架到肩上,领着一家人,从九码头沿着长江沙滩一路向庙嘴走去。看着宽阔的此起彼伏的长江,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,看着长江两岸错落有致的高楼,头一次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我,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,这里,虽没有雄伟绵延的高山,却有着鳞次节比的高楼,幻想着自己将来的新家也一定就是在那些高楼中的某一处吧。
然让我们想不到的是,来到庙嘴,父亲带我们乘快艇踏上了我们宜昌的第一个“家”——一条从日本进口的挖砂船,据父亲说那可是当时他们单位最大的一艘船。父亲的房间很小,除了一张写字桌、一个小衣柜,就只有一张很窄小的高低床,中间还可勉强摆上一张小园桌供一家人站着吃饭。面积虽小,却因一家人能每天在一起而幸福无比。我偶尔从船上看向烟波浩渺的江面,从记忆中寻找老家的模样,新奇、熟悉却又陌生。就这样,我们在父亲的船上开心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寒假。
永远的西坝
在船上生活期间,父亲帮我们联系好了学校,还花400元钱在离葛洲坝大坝不远的下西坝买好了房子。
春节刚过,怀着期待的心情,我们从父亲的轮船搬到了岸上的家——一个低矮的、盖着牛毛毡的、被正在轰隆隆筛分砂石的皮带机围着的、仅三个房间的破平房。想着老家新落成才两年的新居,看着周围高大的楼房,我似乎已没有勇气踏进那个所谓的“家”了。后来才知道这是爸爸单位原来建葛洲坝时工人居住的工棚。葛洲坝建好后,这些工棚保留了下来,一些职工将家属接来纷纷在这些三三两两的工棚安了家。好在母亲的乐观坚强总在激励着我,她说:没什么,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父亲的勤劳任怨感染着我,他说:只要爸爸努力工作,我们会住上楼房的。就这样,一家人便在这简陋的地方安住下来了。只是,没有田,没有山,作为单职工家庭,要想在城里立足,艰辛远比想象的困难得多。
牛毛毡的房子,夏天如蒸笼,冬天如寒窖。尤其是怕过夏天,热倒在其次,而是怕刮风下雨的日子。牛毛毡年代久了,很多地方已腐化,经常是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。有一年夏天,天空似乎是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般,瓢泼大雨倾盆而下,加上地下排水不畅,雨水不停地往屋里倒灌,瞬间就把家里都给淹没了。一家人不得不人手一个盆,不停地从家里舀水往外倒。天明了,雨停了,我们方才停下,而此时才发现,牛毛沾的房顶估计是再也经不起风雨了。父亲的单位也曾几次提出在职工楼分配一间房给我们。可一家五口人,一间房毕竟太小,再加上母亲已凭着过硬的裁缝手艺,在家里一边操持家务,一边承接衣服加工以补贴家用。所以,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搬离,只是四处凑着钱买了石棉瓦,将牛毛沾换了下来。
父亲单位效益似乎是越来越不好了,房子前面的皮带机原来是白加黑连轴转,可渐渐地,皮带机也只是偶尔转转就停。父亲所工作的轮船多数时间也没有生产,他只需每隔几天去船上值守一次,每个月也只能领不到一百元的工资,且分几次发放。我们姐弟仨由于没有户口,除了正常的学费,还得多交借读费。家里经济状况是愈发糟糕,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,父亲不得不起早贪黑到建筑工地去打临工,爸爸好多同事也大都如此,有出去找事做的,有去卖菜的,大家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,直至1989年。
“单位现在不再单一地搞砂石了,听说在外面接了好几个水电站、砂石拌和工程,今天单位通知我到清江隔河岩上班,我准备这几天就走了。家里以后就辛苦你了。”父亲对母亲说到。
“这下好了,有活干了,生计就再也不用愁了。”虽不舍父亲离家,但母亲仍为父亲不再需要到建筑工地干活而开心不已。
父亲去外营点后,他的收入也成倍增加,加上母亲的生意也日渐红火,家里的境况也逐渐好转。父亲所在的单位为了解决单职工住房问题,也陆续建了好些福利性住房,职工只需象征性地支付一笔购房款便会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父母也是有些动心,但养着三个孩子,终究是个不小的负担,而且母亲还是很想在原地方继续从事着她的手艺。是啊,居住条件虽差,但周围那些葛洲坝的叔叔伯伯们却是那么地勤劳、善良、积极、乐观,大家尤如亲人一般,谁家有个困难,大家伙儿总是力所能及地互相帮衬着,或许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心里便有了深深的葛洲坝情结。于是在1991年,我初中毕业那年,家里将房子推倒,在原址重新建起了一栋独门独院的平房,虽简陋却令我欢心不已。
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的向前流逝着,父亲随着工程转战南北,从清江隔河岩到高坝洲,三峡大坝到贵新高速,母亲开玩笑地对父亲说:“你们单位可真是厉害,建电站,修路桥,真个是上天入地,无所不能啊。”
“企业要生存,要发展,守着一棵树哪里行啊,如果我们还是如原来那样只固守砂石,盯着水下,我们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啊,所以,转型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啊。”父亲若有所思地对母亲说到。就这样,父亲在不同的外营点奋战着,用他自己的话说:苦并快乐着。
住进高楼
1997年,大学毕业的我,怀着特别的情结,我放弃了本可以教书育人的教师职业,毅然选择了葛洲坝,成为了一名“葛二代”。多了一个人拿工资,家里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,换房这一话题也逐渐被提上了日程,单位又新建了很多经济适用房,此时的我不觉动心了。可在西坝住了十几年,母亲似乎已与西坝这片岛屿有了深深的感情而不愿意搬离。于是,为了依从辛劳的母亲,我们将平房进行了装修,装修后的房子简陋却宽敞明亮干净,住着倒是惬意得很,以至于我结婚后,在母亲的要求下,我和爱人没有住在他买的房子,而是随着父母住在了一起,直到女儿出生。2003年,父亲退休,母亲也不再做缝纫,老两口专职帮我带女儿了,含饴弄孙,尽享天伦之乐。
因了儿时住高楼的梦想,2009年,在没有事先告诉父母的情况下,我在公司修建的高层住房中替父母买下了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。拿到钥匙那天,满心的高兴与激动,将钥匙郑重地放在了母亲的手里。望着那串闪闪发光的钥匙,母亲眼里噙满了泪花,却嗔怪到:“这么大的房子,得好多钱啊。你不该买啊。”
“妈,您放心吧,公司的经适房比外面的商品房便宜多了。再说了,公司现在经济效益好,每年签约都突破一百亿啦,职工收入都翻了几翻啊。买房首付没有什么问题,后面的用公积金贷款,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您和爸就安心地住吧。”我高兴地说。
“好,好,房子先搁着吧,到时再搬,现在住这里挺方便的。一出门就都是老熟人,热闹啊。”母亲边说边将钥匙小心的收了起来。违拗不过固执的母亲,也暂且随她了。
“听说西坝要修庙嘴大桥,我们这儿的房子要拆,是吗?”2012年11月的某一天晚上,一家人正在一起看电视,母亲问到。
“是啊,我们公司与中铁大桥局组建联合体,以BT方式投资建设。工程马上动工,我们家房子在红线范围内,肯定是得拆。”我说到。
“啥,咱公司现在还搞起投资了啊?那不搞施工了吗?”父亲一脸的疑惑。
“哈哈,爸,我们公司早就开始搞投资项目了。我们老家的云龙河电站、鱼泉电站,就是我们公司投资修建的。还有重庆的綦江高速公路,也是我们以EPC方式参与投资修建的。紧接着就是这个庙嘴大桥了,这是宜昌市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城建项目了。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公司创新商业模式、向产业链高端进军的项目,这些项目的成功运作,让我们公司从以往单纯的工程承包方向既是工程承包商、又是投资运营商的转变。以后啊,我们的投资项目会越来越多呢。”我尽可能地对父亲简单地解释到。
“什么EPC、BOT,我听不懂。不管咋样,只要公司越来越好就行。”父亲迷惑中却又带着些许喜悦之情。
“是啊,我们都期盼着公司发展越来越红火。现在,公司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建筑市场产能过剩的压力,若还固守传统的经营模式,只能被市场所淘汰。所以,创新商业模式,进军高端项目,是公司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”我似乎是在自言自语,又似乎是在对父亲继续解释着。
“那我们就尽快搬到新房子吧。”原想着如何做母亲搬离的劝服工作,不曾想这次母亲却是如此的爽快。“自己公司干的项目,我们做不了别的,但可以早点搬家,让公司快点把项目干完。”母亲说到。第二天便开始忙着收拾家当搬家了,不久后便搬到了新居。自此,我再也不用担心下雨的日子,父母家会否进水这个问题了。我可以悠然地坐在窗下,品一茗香茶,聆听着雨落的声音。
后记:不可磨灭的记忆
西坝的平房随着庙嘴大桥的推进而走向被拆除的行列。看着这座见证我家30年变化的老宅,看着那爬满了金银花的院墙,回想着曾经的愁苦与欢乐,满心的却尽是不舍。拿起手机,拍下了眼前的一切。自此,这个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宅子便定格在了我的手机里,同时也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。
(葛洲坝集团 喻碧)
|